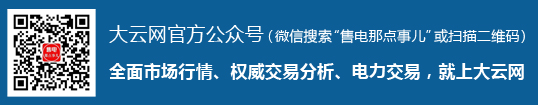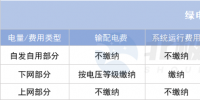转变能源结构,除了要加快不同能源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加大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比重,还要解决能源内部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最关键是要解决煤的利用问题。
上世纪50年代,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为90%以上,6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工业的发展,煤炭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1999年降至67.1%,近年随着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攀升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煤炭比重又略有回升,2011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为68.4%。根据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开发情况和供需变化,有研究者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
煤炭是最“脏”的化石能源,大量污染物如CO2、SO2等都是燃煤排放的,我国由于燃煤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85%左右。在我国目前主要大气环境污染中,一半以上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均来自煤炭。可见,能否实现从“黑色”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将成为对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重大考验。
煤炭占比过高对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暖也将产生严重阻碍,IEA按 “参考情景”预测中国2030年一次能源需求至少将翻一番,其中一半增长源于煤的需求。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高碳燃料煤炭消费增长会引发碳排放的快速上升,自1751年工业化初始至1998年的近250年间,全球碳排放量增长了2200多倍,其中,以煤炭为主导的前210多年全球碳排放量增长最快。
转变能源结构,除了要加快不同能源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加大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比重,还要解决能源内部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最关键是要解决煤的利用问题。
一是要提高煤的使用效率。我国以煤为主要能源是基于我国煤储量丰富的判断,但我国人均煤炭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0%,而且2009年之后我国已成为煤炭净进口国,说明煤炭在量方面的优势已逐渐丧失,因此必须提高煤的使用效率,不能无限度挥霍。要加快煤炭使用能效标准的出台,高能效的多联产路线以及煤化工和石化、冶金等产业的共生路线是实现煤的分级和高效利用的必然选择。针对煤炭资源利用方式单一化、煤化工产业规模小、污染严重等问题,政府应加强对火电厂、水泥厂、焦化厂等的布局规划,尽量减少布设独立的工厂,引导煤、电、化、热、冶、建材等多产业的综合一体化产业群建设。
二是加快煤炭循环利用和新型煤化工业发展。煤炭发电、炼焦和作为工业燃料的生产过程会根据不同用途产生大量的不同排放物,也是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途径,但这些排放物若能加以循环利用,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创造很高的经济价值。例如,我国每年排放掉的焦炉气约为200亿立方米,其中H2/CO的比率能够达到10∶1,可以与煤气化产品调配,用于甲醇等化工产品生产。新型煤化工业正是以资源最大化利用和污染最小化排放为目标的,可以对煤炭中主要化学元素如碳、氢、硫、氧等予以充分回收利用,并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更为重要的是,新型煤化工业对煤质要求不高,可以充分利用大量的中高硫煤和褐煤等劣质煤炭资源,甚至煤渣、煤焦油等废弃资源,将大幅提高我国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应对煤炭资源循环利用和新型煤化工业发展较好的地方和企业给予优惠鼓励政策,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地租优惠、项目倾斜等。
三是加快洁净煤技术开发。洁净煤技术是洁净、高效利用煤炭的先导性技术,是旨在减少煤炭开发利用全过程中污染排放和提高利用效率的煤炭加工、燃烧、转化和污染控制技术,也是国际高技术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世界各国都实行了强有力举措来推动洁净煤技术发展,如美国的洁净煤示范计划、欧洲的兆卡计划、日本设立了洁净煤技术中心等。我国在洁净煤技术开发方面进行了有力引导和支持,如出台《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洁净煤技术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家863计划设立洁净煤技术主题等,我国洁净煤技术取得了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成果。但还存在对洁净煤发展的部门协调不到位、企业激励政策不到位、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消化结合不到位、技术转化和推广应用速度较慢等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加大财政经费对技术攻关、工程示范的投入,搭建平台促进产学研联合,设立科技专项等方式帮助化解洁净煤技术开发和利用中的难题,推进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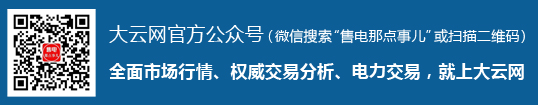
上世纪50年代,煤炭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为90%以上,6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工业的发展,煤炭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1999年降至67.1%,近年随着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攀升以及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煤炭比重又略有回升,2011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为68.4%。根据中国的能源资源条件、开发情况和供需变化,有研究者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不会有根本性改变,煤炭比重仍将维持在60%以上。在这种现实条件下,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
煤炭是最“脏”的化石能源,大量污染物如CO2、SO2等都是燃煤排放的,我国由于燃煤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85%左右。在我国目前主要大气环境污染中,一半以上的总悬浮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以及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均来自煤炭。可见,能否实现从“黑色”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将成为对中国生态文明发展的重大考验。
煤炭占比过高对减少碳排放、应对气候变暖也将产生严重阻碍,IEA按 “参考情景”预测中国2030年一次能源需求至少将翻一番,其中一半增长源于煤的需求。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高碳燃料煤炭消费增长会引发碳排放的快速上升,自1751年工业化初始至1998年的近250年间,全球碳排放量增长了2200多倍,其中,以煤炭为主导的前210多年全球碳排放量增长最快。
转变能源结构,除了要加快不同能源之间的结构性调整,加大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比重,还要解决能源内部的问题,对中国来说最关键是要解决煤的利用问题。
一是要提高煤的使用效率。我国以煤为主要能源是基于我国煤储量丰富的判断,但我国人均煤炭储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60%,而且2009年之后我国已成为煤炭净进口国,说明煤炭在量方面的优势已逐渐丧失,因此必须提高煤的使用效率,不能无限度挥霍。要加快煤炭使用能效标准的出台,高能效的多联产路线以及煤化工和石化、冶金等产业的共生路线是实现煤的分级和高效利用的必然选择。针对煤炭资源利用方式单一化、煤化工产业规模小、污染严重等问题,政府应加强对火电厂、水泥厂、焦化厂等的布局规划,尽量减少布设独立的工厂,引导煤、电、化、热、冶、建材等多产业的综合一体化产业群建设。
二是加快煤炭循环利用和新型煤化工业发展。煤炭发电、炼焦和作为工业燃料的生产过程会根据不同用途产生大量的不同排放物,也是产生环境污染的主要途径,但这些排放物若能加以循环利用,不仅可以减少环境污染,还能创造很高的经济价值。例如,我国每年排放掉的焦炉气约为200亿立方米,其中H2/CO的比率能够达到10∶1,可以与煤气化产品调配,用于甲醇等化工产品生产。新型煤化工业正是以资源最大化利用和污染最小化排放为目标的,可以对煤炭中主要化学元素如碳、氢、硫、氧等予以充分回收利用,并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更为重要的是,新型煤化工业对煤质要求不高,可以充分利用大量的中高硫煤和褐煤等劣质煤炭资源,甚至煤渣、煤焦油等废弃资源,将大幅提高我国的煤炭资源利用效率。政府应对煤炭资源循环利用和新型煤化工业发展较好的地方和企业给予优惠鼓励政策,如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地租优惠、项目倾斜等。
三是加快洁净煤技术开发。洁净煤技术是洁净、高效利用煤炭的先导性技术,是旨在减少煤炭开发利用全过程中污染排放和提高利用效率的煤炭加工、燃烧、转化和污染控制技术,也是国际高技术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世界各国都实行了强有力举措来推动洁净煤技术发展,如美国的洁净煤示范计划、欧洲的兆卡计划、日本设立了洁净煤技术中心等。我国在洁净煤技术开发方面进行了有力引导和支持,如出台《中国洁净煤技术“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纲要》、《洁净煤技术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国家863计划设立洁净煤技术主题等,我国洁净煤技术取得了一批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成果。但还存在对洁净煤发展的部门协调不到位、企业激励政策不到位、先进技术的引进与消化结合不到位、技术转化和推广应用速度较慢等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加大财政经费对技术攻关、工程示范的投入,搭建平台促进产学研联合,设立科技专项等方式帮助化解洁净煤技术开发和利用中的难题,推进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