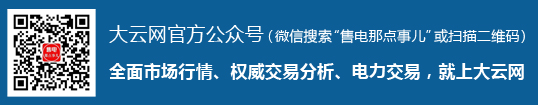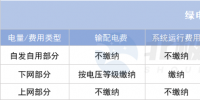《京都议定书》诞生于1997年12月,由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制定。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京都议定书》规定缔约方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在第一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应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5.2%,并且分别为各国或国家集团制定了国别减排指标,具有里程碑意义。
不过,气候谈判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2001年3月,美国政府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将会影响美国经济发展”和“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承担减排和限排温室气体的义务”为借口,宣布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
在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努力下,2005年,经过一系列艰难谈判后,全世界共有180多个国家签署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终于开始生效。
与此同时,第二承诺期谈判启动,一场漫长的“拉锯战”由此展开。在谈判中,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不断讨价还价,提出更多要求,使《京都议定书》第二期签署陷入僵局。
2012年,中国积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协力促成《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通过,并努力争取气候资金支持的延续。多哈修正案从法律上确保第二承诺期在2013年实施,并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所列缔约方规定了量化减排指标,使其整体在2013年至2020年承诺期内将温室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18%。
多哈修正案是国际社会艰苦谈判的成果,维护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特别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公平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延续了《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模式,实现了第一承诺期和第二承诺期法律上的无缝衔接。
在积极参与气候谈判的同时,中国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将其作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入国家发展规划,开展了大量适应和自主减缓行动。2014年6月2日,中国向联合国交存了《京都议定书》多哈修正案的接受书。
但是,美国以及逃离《京都议定书》的加拿大、不加入第二承诺期的日本、新西兰等国,不但拒绝接受提高减排力度和透明度方面的要求,同时还阻挠气候资金、绿色技术转让等谈判的进展,一如既往地游离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阵营之外;第二承诺期的减排雄心不足、环境漏洞突出,减排效力大打折扣;发展中国家关切的气候资金等重要问题也并未得到妥善解决。
这些因素都导致后《京都议定书》阶段的气候谈判形势更加严峻。
在国际气候秩序新旧交替的时代,更需要中国展现大国风范和领导力,为促成全球气候行动注入更大的推动力。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举步维艰。通过与国内的NGO、国际智库等的交流合作,中国代表团在之后历次气候大会上活跃起来,中国角也成为最精彩最活跃的国家展台之一。
从2012年“十二五”规划开始,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智库更多地采纳了中国节能减排目标的建议,包括二氧化碳强度目标、能源总量限制和碳交易试点,都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亮点,中国的减排努力逐渐被国际社会所认可。
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前,中美两度联合发表气候声明,与欧盟以及英法德等主要发达地区和国家也达成双边声明,凝聚共识,对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起到了实质性推动作用和强大的示范效应。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期间,中国积极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获得各方赞赏。巴黎大会也再次印证了中国在气候议题上越来越开放与自信,在南北国家之间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协调作用,促进了不同阵营集团的互信与共识。
2015年12月,里程碑式的《巴黎协定》达成。这是史上第一份覆盖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减排协定,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迈出了历史性的重要一步。《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定。
由中国坚持的敦促发达国家提高其资金支持水平、“制定切实的路线图”等内容被写入决议,确保发达国家2020年前每年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支持的承诺不至于流于形式。
《巴黎协定》是在总结公约和《京都议定书》20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后达成的,凝聚了无数政治家、谈判代表和智库的心血和智慧。但这不会是全球环境治理的终点,应对气候变化不只需要目标,更需落实。正如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在巴黎大会闭幕会议上所言:“一分纲领,九分落实。协定已经谈成,下一步的关键任务是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