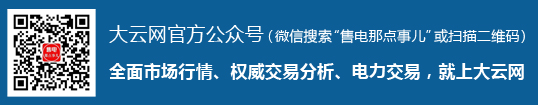一、为什么提“国家能源转型”?
当前,各国能源转型实践各有特点,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我们使用“国家能源转型”,这个提法,主要是想强调:
第一,当前能源转型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议题的背景下,在减碳目标约束下,各国政策推动的能源转型。这与历史上主要由市场自发驱动的能源转型不同。因此,本次能源转型实际上是一个“早产儿”,不是市场和技术的自然产物,必然会带有很多不同于“顺产儿”问题。这是认识当前能源转型各种问题的起点。
第二,强调“国家”,是想强调不同国家能源转型的“特点”和“本地化路径”。因为各国能源转型的条件和起点不同,决定了实现终极转型目标的路径和措施必然是本地化的,才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比如,德国坚决推动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而美国则强调向清洁能源转型。再比如,德国能源转型发展到今天发现电网长距离输送能力成为瓶颈,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今天也要把这个问题放到最为优先的位置。
二、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有效推进国家能源转型的前提
要完整理解国家能源转型,我想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能源转型不仅仅是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或者非化石能源比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源体系的转变。也就是说,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点。没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适应性变革,现有能源体系容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只有把能源体系变革作为能源转型的一个核心要求,才能更好地理解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正确方式与真实空间。
其次,每一次重大能源转型都会涉及到利益再调整,都会产生失败者和成功者。在这一过程中,被替代者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游说政府的支持。如果政府不能把握能源转型的方向,正确处理利益集团“游说”问题,有可能会制定和实施阻碍能源转型的政策。比如,19世纪初,当荷兰传统主导能源“泥炭”的消费地位受到进口煤炭威胁时,荷兰政府采取征收煤炭进口关税等措施,来保护本国泥炭产业。结果不仅延迟了荷兰能源体系向煤炭转型,而且使本已开始衰退的荷兰经济雪上加霜。
最后,对当前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清晰认识和足够重视,尤其是电网系统要主动进行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要求。从长期性看,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并获得主导地位,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时间。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从复杂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个品种的集合,其中任何一个能源品种都不具备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而且,这些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也不完全相同。要将这些能源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新”能源体系,将要处理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问题。
三、我国当前能源转型的难度与复杂性对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国当前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还处于爬坡阶段,能源结构还处于煤炭时代,而世界已经处于石油时代,等等。这里,我想从更为一般的层面强调国家能源转型的难度与复杂性对政策的三个挑战。
一是政策的系统性挑战。这是以大规模、高能量密度、生产消费分离为特征的化石能源体系与适度规模、低能量密度、生产消费靠近、甚至合一为特征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别带来的政策挑战。新的能源体系不能完全通过现有化石能源体系的外延扩张而形成。这对能源转型政策的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政策的适度性挑战。这主要是指政策推动的国家能源转型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是:政策鼓励的技术方向可能与市场选择的不一致,或者政策对某一方向过度支持而妨碍了更好技术的产生,从而导致能源转型成本高昂,甚至锁定在劣等路径上。在碳减排目标的压力下,政府很有可能选择强力推动短期内看起来容易见效但缺乏前途“技术路径”,抑制真正有发展潜力,但短期内不容易见效“技术路径”。这对政策介入转型的方式和程度提出了挑战。
三是政策的协调性挑战。从当前国家能源转型的方向和目标看,系统灵活性是未来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稀缺资源,而我国当前能源体系灵活性和效率提升不仅面临技术方面的障碍,而且也由于市场化改革迟缓而面临体制障碍。因此,为降低能源转型的成本与阵痛,需要加强当前能源体制改革与能源转型政策协调,在体制改革中融入能源转型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能源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电力市场化改革,是有效推进国家能源转型,降低能源转型成本的必要条件。
(来源:在2015年度能源软科学优秀成果交流会上的发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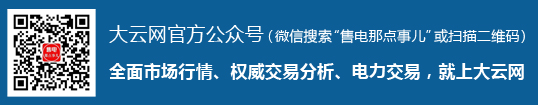
当前,各国能源转型实践各有特点,但“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是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我们使用“国家能源转型”,这个提法,主要是想强调:
第一,当前能源转型是在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主流议题的背景下,在减碳目标约束下,各国政策推动的能源转型。这与历史上主要由市场自发驱动的能源转型不同。因此,本次能源转型实际上是一个“早产儿”,不是市场和技术的自然产物,必然会带有很多不同于“顺产儿”问题。这是认识当前能源转型各种问题的起点。
第二,强调“国家”,是想强调不同国家能源转型的“特点”和“本地化路径”。因为各国能源转型的条件和起点不同,决定了实现终极转型目标的路径和措施必然是本地化的,才是最有效和成本最低的。比如,德国坚决推动能源体系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而美国则强调向清洁能源转型。再比如,德国能源转型发展到今天发现电网长距离输送能力成为瓶颈,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今天也要把这个问题放到最为优先的位置。
二、完整理解能源转型的内涵是有效推进国家能源转型的前提
要完整理解国家能源转型,我想强调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能源转型不仅仅是单纯提高可再生能源比重,或者非化石能源比重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源体系的转变。也就是说,与化石能源特性完全耦合的现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必须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分布式、小功率特点。没有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适应性变革,现有能源体系容纳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空间相当有限。只有把能源体系变革作为能源转型的一个核心要求,才能更好地理解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正确方式与真实空间。
其次,每一次重大能源转型都会涉及到利益再调整,都会产生失败者和成功者。在这一过程中,被替代者会采取各种措施来游说政府的支持。如果政府不能把握能源转型的方向,正确处理利益集团“游说”问题,有可能会制定和实施阻碍能源转型的政策。比如,19世纪初,当荷兰传统主导能源“泥炭”的消费地位受到进口煤炭威胁时,荷兰政府采取征收煤炭进口关税等措施,来保护本国泥炭产业。结果不仅延迟了荷兰能源体系向煤炭转型,而且使本已开始衰退的荷兰经济雪上加霜。
最后,对当前能源转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有清晰认识和足够重视,尤其是电网系统要主动进行变革以适应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要求。从长期性看,一种能源替代另一种能源并获得主导地位,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时间。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从复杂性看,可再生能源是多个品种的集合,其中任何一个能源品种都不具备成为单一主导能源的“潜质”。而且,这些可再生能源品种的技术特性也不完全相同。要将这些能源技术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新”能源体系,将要处理更多的技术、组织和制度方面的复杂性问题。
三、我国当前能源转型的难度与复杂性对政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我国当前能源转型的复杂性和难度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能源消费还处于爬坡阶段,能源结构还处于煤炭时代,而世界已经处于石油时代,等等。这里,我想从更为一般的层面强调国家能源转型的难度与复杂性对政策的三个挑战。
一是政策的系统性挑战。这是以大规模、高能量密度、生产消费分离为特征的化石能源体系与适度规模、低能量密度、生产消费靠近、甚至合一为特征的可再生能源体系之间的巨大差别带来的政策挑战。新的能源体系不能完全通过现有化石能源体系的外延扩张而形成。这对能源转型政策的系统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是政策的适度性挑战。这主要是指政策推动的国家能源转型面临一个很大的风险是:政策鼓励的技术方向可能与市场选择的不一致,或者政策对某一方向过度支持而妨碍了更好技术的产生,从而导致能源转型成本高昂,甚至锁定在劣等路径上。在碳减排目标的压力下,政府很有可能选择强力推动短期内看起来容易见效但缺乏前途“技术路径”,抑制真正有发展潜力,但短期内不容易见效“技术路径”。这对政策介入转型的方式和程度提出了挑战。
三是政策的协调性挑战。从当前国家能源转型的方向和目标看,系统灵活性是未来能源体系(特别是电力系统)的稀缺资源,而我国当前能源体系灵活性和效率提升不仅面临技术方面的障碍,而且也由于市场化改革迟缓而面临体制障碍。因此,为降低能源转型的成本与阵痛,需要加强当前能源体制改革与能源转型政策协调,在体制改革中融入能源转型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能源市场化改革,特别是电力市场化改革,是有效推进国家能源转型,降低能源转型成本的必要条件。
(来源:在2015年度能源软科学优秀成果交流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