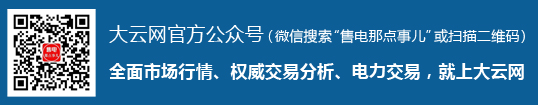“分享红利”无疑是本轮电改的关键词,也必然是地方政府最为迫切想要去落实的关键项目。但“分享”本身的核心终究在于“红利”的客观存在,离开了这个根本谈“分享”的方式方法技巧则只能是一个伪命题。以2016年上半年为例,煤价水平是2012年的一半左右,而这四年半中消失掉的一半煤炭收益实质上就构成了贵州2016年整个电改红利的基石。但价值规律告诉我们“出来混迟早要还的”,截止到2016年末,煤价水平已经基本恢复到2012年的水平,标煤均价超过600元/吨,“毛之不存,皮之焉附?”,所谓基石已然“石沉大海”。电改让利的地方导向性能源策略在此种局面下如何“破”的问题横垣在电改决策层的面前,破、立因果非常道也,且容小编抽丝剥茧、慢慢道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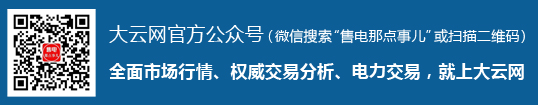
“红利”之“红”即可看作政策之“红”,以“中发9号”及配套文件为引领,地方实施细则为抓手,可以说经历三年的演进,贵州电改政策由“邯郸学步”到自成一体,政策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都在不断增强,可圈可点可赞之处点点滴滴来之不易,其间的博弈与艰辛个中之人体会颇多。可是市场合理平稳运行边界条件的不可控性实非设计者们的初衷,但这种不可控却又实实在在的干扰了电改前行的脚步。既然政策支撑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性目的地,那么“解铃”之道则只能回归于“红利”之“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嚷嚷、皆为利往。”古语所言实质上道出了市场经济的真谛,“红利”之“利”即为市场之利,利者有私利亦有公利,公私一统方为天下之归心、民心之所往。那么电改“红利”之“利”如何在2017年进行重建就是破局的关键所在,“九层之塔,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重建还是应该由解构正型开始。
“红利”的构成在当前的能源产业链上是由四个节点构成的,当前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煤炭产业,作为红利供给的源头,煤炭企业给整个能源产业链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随着年底的煤价翘尾,煤炭又把输出的红利以煤价暴涨的方式进行了粗暴的回收,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但我们也应该理性的看到,煤炭市场的这种非理性上涨其可持续性堪忧,而且贵州煤炭的长期成本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人工成本、资金成本、税费、规费等硬性支出依然左右着煤炭吨煤边际。当前贵州典型煤炭企业的煤炭生产成本应在320-380元/吨左右,在整体经济形势较为严峻的情况下,考虑煤炭企业6-8%左右的合理利润率,则煤炭企业愿意接受的煤炭交易价格在340-410元/吨(含税)之间。从目前毕节、六盘水、安顺等贵州主要产煤区域政府主导的长协谈判价格来看,基本在425-450元/吨(含税)左右,基本达到且略微超过了煤矿企业的期望值。也就是说如果低于这个价格区间,煤矿企业将失去生产积极性,整个煤炭行业必然会像2016年上半年一样,在价格杠杆的驱使下自动减产,偏离电煤供给与需求的平衡范围。在此情况下,煤炭侧的红利空间显得极为狭窄。
二是发电产业,本来是煤炭红利转移者角色却随着煤价暴涨演变为了电改红利的绝对供给者,其间冷暖发电自知。2016年年末,标煤单价高达630元/吨,按火电机组当前年利用小时4000小时测算,火电发电单位成本合计高达0.35-0.39元/千瓦时。而现行火电上网标杆电价对应的不含税电价为0.2874元/千瓦时,现行标杆电价明显偏低,已与发电成本倒挂。同时,省内燃煤发电企业参加“西电东送”的电量与电网企业结算电价为0.3149元/千瓦时(含税),该部分电量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资金(0.0137元/千瓦时)由发电企业缴纳,进一步降低了标杆电价水平。因此火电企业参与直购电交易的可挤压红利已经基本趋于零。
三是输配侧,2016年电网侧外报数据工业企业输配电价同比下降1.6分/千瓦时,按此测算电网企业2016年在直接交易过程中让利5亿元左右。输配电价让利让电网也感觉有些不堪重负,但其中部分原因则是因为网损价格中交易过程没有得到体现,按照2017年已经确定执行的综合网损率4.38%计算,含网损的输配电价将在2017年的电力直接交易中提高1.3分/千瓦时左右,基本弥补了2016年电网公司让利价差损失,在包含网损以后输配电价在2017年将回到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但应该客观的看到各个电压等价之间由于批复输配电价和初定的各等级网损率的差异,使得电网企业在不同电压等级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用火电标杆电价与工业用户目录电价的采购价差,与火电厂与用户直接交易以后电网获取的输配电价(含网损)收益作比较可以发现(火电厂交易电价按照不降价的交易基准电价计算),20KV及以下用户参与直接交易,电网企业获得的收益高于此类用户不参与交易时的购销差价收益;而20KV以上用户参与直接交易,电网企业获得的收益低于此类用户不参与交易时的购销差价收益。
四是用户侧,2016年对于贵州大工业用户而言是绝对且唯一的红利分享者,一方面按照交易均价测算,整个发、输电行业为“输血”40亿元左右(估算数);另一方面,在去产能的大背景下,电解铝、电解锰、铁合金等高耗能产业终端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以电解铝为例均价上涨近20%,成本与收入双向得益,但随着火电燃料边际的衰退,工业企业的电价成本获利也将在2017年大幅缩减。另外,也应该客观公正的看到,在电价让利的前提下,贵州工业企业托举起了一个100亿千瓦时的增量用电市场“蛋糕”,从社会总红利的角度而言,工业企业用电户也是全社会边际红利的供给者。
从上述解构分析可以看到,煤炭企业由电改红利供给者逐渐演变为去产能红利受益者;火电企业由红利转移输送分配者变化为电改红利绝对供给者;电网企业在2017年将回归到红利输送分配中立者;用户侧则是扮演着者电改红利受益者和全社会边际红利供给者的双重角色。
解构至此,对煤炭市场边界畸变的“破局”问题似乎能看到一些曙光,或者说一点应对之法。我们可以尝试这样来看待红利的问题:把历史的低煤价边际空间看作是全社会的存量红利,把托举起来的工业用电量看作是全社会的增量红利,再把存量与增量的勾稽关系进行一下推演,具体如下:
煤炭市场价格经历了由高到低再由低到高起伏跌宕,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电改源头红利的释放到回收的过程,这和当前美元的加息回笼全球资本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如果把红利流动看作是资本的流动,那么资本利润必然也随着资本的流动向着煤炭源头集聚。但这是对电改存量红利的快速抽蓄,煤炭下游产业——火电和用户必然在此时将经历倒输血的阵痛;同时电网企业的网损电价回归同样是在2016年整个存量电改红利的盘子中分食收益;而用户在低价电收益缩减的情况下,其产量释放肯定会受到波及,这就意味着电改的增量边际红利受到威胁,边际红利的发源地出现问题以后,其结果又将叠加影响到全产业链的红利分享进程,进而对电改本身造成伤害。以上三者的勾稽关系可以说明,整个产业链条上任何一点的价值流动集聚发生突变,如现下的煤炭市场,在短期内对集聚的节点而言可以带来暴利,但绝对不可持续,长期影响必然是负面的。
鉴于此,是否可以考虑如下措施来化解当下的产业链条价值的矛盾:
一是通过合理的长协价格疏导使得煤炭价格逐步趋于理性,同时对国有大矿的煤价执行进行严格的监管,强调契约精神,以占30%权重的国有煤矿产能作为杠杆稳定整个煤炭市场价格水平,并锁定一个煤价基准如环渤海指数进行合理的波动微调,确保煤炭下游产业价值链不被煤炭市场继续“抽血”。同时,进一步加大煤炭产业“清费立税”力度,为煤炭企业减负,从而扩大电改源头红利;
二是对电网企业今年新增的网损价格进行分类疏导:首先在确保电网网损总收入不变的前提下,维持综合网损率4.38%不变,适当调整各电压等级网损率,使得低电压等级网损率适当降低,高电压等级网损率适当提高,使得各线路等级的工业用电户的网损价格均衡性得到提高,既不损害电网的利益,又扩大了电改红利的覆盖范围(贵州省低电压等级工业用电户数量占比超过70%);其次,对于周边跨省交易的输配电价进行合理疏导,在当前国家并未对跨省输配电价进行核定批复的情况下,应该在省内批复的输配电价上进行适当下浮或者维持原输配电价不变,以此来托举跨省交易的增量市场或者说增量红利(2016年跨省直接交易占交易电量比重15%左右)。此举虽然存在对外省能耗企业输血增强其与本省能耗企业竞争力的弊端,但这种负面影响相对于当期托举省内煤、电两个市场而言存在相对滞后性和损益差别。
三是对于火电企业采用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进行适当补血,比如在煤炭采购环节继续采用购煤补贴、存煤补贴的方式等直接方式;在电煤运输环节上开绿灯降低电煤运输成本;在“西电东送”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基金上减免收取或延迟收取,从而降低火电厂电价损失或资金成本;在电费回收环节上进行监管和干预,保障火电厂电费回收周期,控制承兑汇票的支付等。从而最终确保电改红利的供给者——火电厂的红利贡献能力。
四是对于用户侧,进一步落实降低实体经济成本的国务院文件精神,从税费负担、融资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人工成本、物流成本等多个方面为实体经济减负,从而确保在煤价、电价存量红利衰退的情况下,工业用户产量不减、用电量不减、全社会电量边际红利不减。
一双健康的“市场之手”就是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兼顾长期效率和短期效率、兼顾能源市场上的每一个贡献者和耕耘者。对于一个长期均衡发展的电力市场而言,“分享红利”并不是一个准确和合理的词汇,真正理想的描述应该是“共享红利”,只有当市场上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成为红利供给者和红利分享者时,才能够体现电改市场的存量红利分配机制的成熟与合理、市场增量红利制造机能的全面复苏。
“阳光普渡、雨露均沾”,电改应只是一个能源普惠的起点而非利益分配的牌局开端,就像某位诗人所言:“我们不要走得太远,忘了当初出发的目的”。